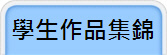移民人權:族群與多元文化的觀點
Human Rights for Immigrants: Ethnic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備註:學生名字皆以匿名方式處理]
翊茹的族群經驗與族群認同
一、前言
我從小就知道自己是外省人和客家人所生的小孩。我的爺爺、奶奶都是湖北人,他們在民國36年來到台灣,住在台北市○○○的○○○宿舍長達28年,直到那邊要蓋中正紀念堂,他們才搬到○○○路,也就是我現在的戶籍地。而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客家人,他們住在台中縣的○○鎮,外公以木材生意起家,並在梨山買了許多土地,轉行當果農,我母親的兄弟也都繼承了外公的事業。我的父母親婚後和我的爺爺、奶奶住在一起,直到生下我,才搬到台中市過核心家庭的生活。我記得上小學以後,我跟哥哥每年寒暑假都會回台北跟爺爺、奶奶一起生活,因為父親常說台北才是我們的「家」。果然當父親結束台中的工作後,我們全家又搬回台北與爺爺、奶奶同住。
我想探討在這樣兩種族群的結合下,父系的外省文化和母系的客家文化對我有怎麼樣的影響,我又會如何形塑我的族群認同,以及母親嫁到外省家庭,對她與客家文化原生家庭的連結有何變遷,是否會影響到我對客家文化的認同?最後,國語在我成長過程中的象徵意含以及背後的結構性優勢也是我以下會探討的議題。
二、身為外省小孩
當我在台中念小學時,每年寒暑假都會回台北跟爺爺、奶奶一起生活,這增加了我與他們相處和瞭解的機會,也更體會到身為外省人的族群經驗。我記得10歲時,第一次陪奶奶去美髮店洗頭,當時我覺得洗頭髮的工作真是太有趣了,而且可以幫客人「編頭髮」,於是我就跟奶奶說,我長大以後要當「洗頭小妹」。沒想到回家以後,我被爺爺大罵一頓,說我們外省人家的小孩將來都是知識分子,怎麼能去做那種工作?叫我打消當「洗頭小妹」的念頭。接著我爺爺在那個暑假每天發給我一張稿紙,要求我一天寫一篇作文,題目像是「路」、「志向」之類的,寫完後由我爺爺檢閱,那時我以為不好好唸書、不會寫文章,就不配當外省人家的小孩,整個暑假過得戰戰兢兢的。
回頭想想,我爺爺會這麼大動肝火,期許我未來成為知識分子,也跟整個外省家族在階級上的優勢有關。我奶奶以前在大陸是師範大學畢業,而爺爺是黃埔軍校第○○期的軍人,他們兩人在大陸時,通信長達3年多,因寫信而相戀到結婚,我親戚常誇我爺爺文筆好,才能追到富家出身的奶奶。我奶奶來到台灣後,在小學當老師,並在電視台當製作人跟編劇,她一生所教的學生與提拔的演員不在少數,她最讓我佩服的地方是她獨自扛起養育四個小孩的重擔,照顧身體不方便的爺爺,以及栽培四個小孩出國唸書,我的父系長輩也都屬於中產階級,像是教授、作家和出版社發行人等,我爺爺常說外省家庭的文化和家教是有深遠影響的,我所接觸到的其他外省長輩,大多數在社會上的確享有較高的階級,我長大後漸漸能了解外省家庭的優越感,或許就是源自文化與階級上的優勢。
在文化方面,我的長輩特別注重小孩子的餐桌禮儀和規矩,我記得小時候,筷子拿不好,是會被長輩打下去的,更別想吃飯。拿筷子的姿勢一定要正確,而非會拿就好了,久而久之,我就養成了大人眼中「標準」的拿筷子姿勢,我也沒有察覺何謂正確或標準,直到大學時和一群朋友吃飯,有個女生主動說我拿筷子的姿勢好「標準」唷,我才發現我跟別人拿的方式的確不同,我的每個手指都有明確的位置,而且我不會發生夾不起食物的狀況,她還說:「你是外省人嗎?你家教很嚴,對不對?」那次是我第一次察覺有這樣本省、外省的區分,她說她們家(本省人)都沒有教,都隨便拿,這樣的經驗無意間勾起我小時候曾經被嚴格教導的回憶,也認同自己所受到的外省文化影響。
從我生出到18歲為止,主要是居住在台北市和台中市,家人和鄰居間都是用國語來交談,我只依稀記得,每當我陪母親去吵雜、髒亂的市場買菜時,總會聽到她突然用我聽不懂的語言,流利的和攤販殺價,等我再長大一點,才知道母親跟他們對話的語言是台語,但我打從心裡不太喜歡台語,總覺得那不是我該學的語言。從小到大,我母親也從未教過我講台語或是客家話,當我跟哥哥回○○鎮看外公、外婆時,他們也都是用國語來和我們交談,所以我從小的母語就是國語,偶爾藉由看電視才聽得懂很基本的台語,但我完全不會講客家話。從小學到高中,我和同學都是用國語交談,鮮少聽到同學使用台語,更遑論客家話了。直到我到花蓮念大學,才首次接觸到來自南部的同學,我記得有一次,當我聽到兩個男同學用完整的台語在對話,我一臉吃驚的打斷他們,問他們幹嘛突然講台語呀?他們說從小到大在高雄都說台語呀,這樣會很奇怪嗎?我搖搖頭說不會啦,只是覺得好特別唷。大體來說,不會講台語或客家話這件事,並未帶給我生活上的困擾,從小我也一直傾向認定自己是個只說國語、不說台語、不懂客家話的外省小孩。
回過頭來分析,我小時候所居住的地點是在台中市的○○附近,那邊的居民多是教師和退伍的外省軍人,所以在地理環境上,就是以國語為主的軍公教社區,我很自然的就只有接觸國語,並習慣使用國語。而我兒時記憶中的菜市場是一個吵雜、髒亂的環境,攤販的穿著比較隨便、談吐比較粗魯,和「我們家」很不一樣,所以當平常跟我用國語交談的母親,一到了菜市場,卻突然轉換用攤販慣用的台語去交涉時,這會讓幼小的我將台語和菜市場攤販的形象連結在一起,並視台語為階級較低、較不入流的語言,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小時候打從心裡不喜歡台語,甚至覺得那不是我該學的語言,因為我會覺得菜市場攤販的階級和我從小生長的外省家庭不一樣,我不需要去學「他們」的語言,但其實菜市場是一個族群混合的聚集地點,當時的我,並沒有族群多樣性的概念,只是很本位的認為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有一種外省家庭的階級優越感,因為我的父系家族都說國語,教育水平都比較高,所從事的職業、穿著、打扮都優於他們,或是比較「文明」,這樣的想法深深影響了我對說國語的外省家庭的認同。而我國中和高中都就讀於台北市的○○區,我們同學間都是用國語交談,但事實上,有各式各樣的族群聚集在台北市,有些同學其實不只會說國語,還會說台語跟客家話,我就知道有同學是從三重跟中壢搬來台北市的大安區就讀,她們的母語都是台語,但因為在台北市這樣一個都會中心,講國語被視為優雅、高尚的象徵,更是學校裡主流的語言,所以大家都說國語,這讓我主觀的將國語擺在主流的位置,以致於當我南部的大學同學以台語交談時,我會那麼沒禮貌的打斷他們,還質疑他們幹嘛「突然講台語」,甚至會覺得他們這樣好特別,但其實是我自己落入了以國語為中心本位的思惟,我不習慣聽到有人說自己不熟悉的語言,並忽略了台語其實是不同族群溝通、慣用的語言之一,我甚至還貶低了台語的價值,我應該要學著解構這樣邊緣他者(台語),突顯自我(國語)的二元對立,重視台語以及每一種族群語言的價值,正視說國語背後的結構性優勢,包括外省人執政,推動說國語的政策,以台北市為中心所建構出來的優越的、先進的象徵。
此外,我的外公、外婆從來不跟我說客家話,而選擇用生澀的國語和我交談,其實牽涉到性別的面向,因為他們認為我母親是嫁出去的女兒,已經是「外人」了,「外人」的小孩就算不學客家話,也沒有關係。身為客家人的母親被她的父母視為嫁離開家的女兒,外公的事業也都依照傳統讓我母親的兄弟繼承,逢年過節,我母親幾乎都要待在台北的家,依夫家的規矩,服伺我的爺爺、奶奶,照外省人的傳統打麻將、煮外省家鄉的年菜,很少有機會回○○過節,客家的傳統文化和我母親的連結也不再那麼強烈,到我這一輩,對於身為客家人的認同就更為薄弱了,尤其是完全不懂客家話這一點,讓我無法完全認同自己是客家人。
在文化上,由於我從小就和父系外省家族的爺爺、奶奶的相處經驗較為深刻與豐富,而所受的影響也較為深遠,相較於母親被視作嫁出去的女兒,以及我對客家語言、文化上的認同與體驗的薄弱,我會偏向認同自己是個外省人;此外,對於說國語的象徵意含,從小時候我對台語與菜市場的連結,影響我對台語的觀感與認知,加上居住與就學的地理位置,造成我把國語視為主流語言,也強化了我身為外省族群的階級優越感,然而,我明白的發現,其實我落入了以國語為中心本位的思考邏輯,我忽略了台語也是不同族群溝通的語言之一,在台灣這片土地上,還有原住民、外籍朋友、客家人等族群的語言在被使用著,我應當正視說國語背後隱含的結構性優勢,去解構排除其他語言,突顯國語優勢的二元對立,藉由重視每一種族群語言的價值與意義,來批判國語的主流位置。
|
本計畫由教育部 「新移民與多元文化計畫」顧問室支持 |
|
Program iSCD Office is supported by MOE. |
|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copyright ©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
|
如有任何問題請與網站管理員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