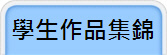移民人權:族群與多元文化的觀點
Human Rights for Immigrants: Ethnic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備註:學生名字皆以匿名方式處理]
宛茹的族群經驗與族群認同
本省人與半個外省人的小孩
回想起我的小時候,我其實沒有什麼明顯的族群認同,一個小孩子會知道大概也只有“我是生在台灣的人”這樣的概念,不同於美國有明顯種族區別的外顯特徵,要從外表來區分族群對我這個生長在周遭沒有明顯不同於漢人的其他族群的小孩似乎有點困難,不過對於用外表來界定族群我曾有一個有趣的經驗,印象中應該是小學高年級時期,曾經有一個社會科老師在課堂上問我:「妳有日本人血統嗎?」,我回應沒有但我媽媽是半個外省人,老師就說:「妳看起來不太像純正的台灣人。」,而這個經驗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我一個對族群概念粗淺的入門知識—就是外表可以部分說出族群的不同之處,並同時意識到我是一個本省人與半個外省人家庭的小孩,所以外省人的概念應該也是從這個時候才被我認真意識到,至於看起來不像是純正台灣人的評語對於我的認同並沒有造成太大陰影,原因是家庭大部分決定了我的族群認同。
家庭作為一個族群認同的指引
我的家庭成長環境,父親是個本省鄉村長大的小孩,對於他自己是本省台灣人有強烈認同感,這從每次觀看電視新聞他對外省人負面情感的表現可以察覺,而且他有國民黨就等同於外省人的政黨這概念,可以推論他是深綠支持者。而我的母親是個在台灣長大的半個外省人,‘芋仔番薯’她會這樣說自己,相較於父親,她在政治上顯得不那麼狂熱與極端,偶爾還會對父親的不理性指責外省人作出一些合理的質疑與糾正,但對於她確切的族群認同我並無法確定,只能些許從她也慢慢被父親的政黨立場拉攏,感覺到她應該比較傾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或許其中可能存在某些曖昧模糊,只是我沒認真詢問過她。因此,在我的家庭政治的立場其實能明顯說明家人的族群認同。就前面所述,雖然我是個本省人與半個外省人的小孩,但並沒有造成我的認同困難,也就是說,我能很直接地去認同父親的台灣人身份而非母親,這很大部分是受到父權意識影響,小孩以父姓命名就會自然去認同父親,且媽媽身為半個外省人卻並沒有特別希望我去能認同自己有一部分是外省人,使得我在談到族群認同上自然就不會想到自己可能是外省人。若我媽媽同時也影響了我的族群認同,或許我會產生對台灣人這個強烈認同些許的質疑,只是她並沒有發揮這樣的功能。
語言使用、族群認同與城鄉差異
對於外公是外省人的印象我依稀只記得小時後曾聽過外公用我聽不懂的福建話和他的友人聊天,那個時候我會意識到外公會說一種我陌生的語言,這突顯了我跟他的不同,讓我知道他是從對岸福建省移民過來的,至於日常溝通大多都還是講閩南話與國語,周遭人都講閩南話而福建人的他也會講,所以並沒有太大衝突。他不會教我說福建話,我也不會主動想要學,我沒想學福建話則是大環境下福建話並非主流語言,沒有學它不對我造成什麼利害影響。我知道我身上有著四分之一的外省血統但因為文化上的連結過於薄弱,於是我就沒有想過自己會可以稱作是一個外省人,頂多勉強以有血緣聯繫之名稱自己為本省與外省結合的台灣人。在這裡除了看到語言是族群認同重要元素之一,也從我因為福建話不符合主流需求而不會主動想學看出族群認同行為背後牽涉更大的政治利益,當國語與閩南語是主流就會犧牲另一個也可建立族群認同的語言學習機會。因此建立族群認同不單只關乎了解一個族群文化與否,有時也與所處社會環境脈絡中的重要利益相關聯,非主流的族群文化就易被族群中心主義所遺忘。
除了這個語言文化影響族群認同的經驗之外,在中學時期,同儕間會不會說閩南語對我來說也是個族群象徵,這樣的推論難免有過於狹隘之嫌,因為會說閩南語並不一定代表你是本省台灣人而非外省人,事實也有台灣人是不會說閩南語,也有外省人是會說的,但因家庭中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的直接連結使得具有閩南話能力某部分有加強我自己台灣人的認同,不過我也不會認為不諳閩南語就不是台灣人或一定是外省人,畢竟語言的使用牽涉許多環境因素。
環境因素中有北南城鄉差異的狀況,這也使得我在北部與南部兩地對自己身為台灣人的認同強弱程度有所不一。在北部唸書時,同儕間會說國語但不說閩南語佔大多數,而可能有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卻不會說閩南語的情形,這與台北人都普遍使用國語而非閩南語有極大關係,國語作為官方語言在台北這個政經學術中心被認為是標準且高尚的,形成講國語的台北人與講閩南語的南部人的區分。在台北,我以會講閩南語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可卻也因為大部分時間仍是講大家認為「標準的」國語,而感到自己雖聲稱是台灣人但潛意識並非完全正向地以會說閩南語而感到光榮,我想這是和國語與閩南語如何在北部以都市中心角度去觀看有關。到了今年南下高雄唸書,我察覺週遭環境絕大多數都以閩南語進行完整的對話(校園裡的發現是最讓我驚奇的!),才進而去反思自己以往在北部的台灣人認同到底內容是什麼,與這些會說閩南語也實際有在使用它的南部人相較起來,似乎以語言來界定我族群認同的強度也不再如我身在台北認為的那樣大。我之前所認同的台灣人是會說國語(應該是因為身在台北所以沒考慮到會有人不說國語)也會說閩南語,這樣使得我看起來比不會說閩南語的台灣人更有資格作為台灣人,可是從我不常說閩南語的情形也反應了台北人並不把閩南語視為合乎標準、可以日常普遍使用的,這樣的認同行為其實是以都市中心角度出發,要到了南部後才發現原來的台灣人認同與南部人所謂台灣人認同似乎有些差距。
年輕一輩同儕間的族群界線已不如上一代因政治歷史造成對立那樣明顯,許多日常真實的互動使得我們並不那麼容易察覺對方族群身分,就像前面所說在台北校園裡學生幾乎都是講國語,要以語言做區分指標就難以達到。而大部分關於省籍族群的圖像多是來自課堂知識或資料閱讀,也有一部分是從媒體與政治意識形態塑造出來的想像(就像是會覺得外省人都會想要回歸對岸祖國,他們在台灣只是短暫的停留等等有所偏頗的刻板印象),但這在同儕間並不一定會引起對立,有可能的話也大多是在選舉時才會被討論。不過我也同時意識雖說同儕間族群界線不易被察覺而沒有衝突,但這正也顯示年輕一輩多數並無法深刻感受自己族群的文化內容,因為我們已經沒有像上一代生活在充滿族群對立的氛圍之中,比如像是昔日的國語政策使得很多台灣小孩不能在學校說閩南語,相信當時的小孩族群意識一定比現在來的高,而現今年輕一輩已少了那樣的政治環境,彼此間就不太去察覺差異,但看不到差異並不代表多元已被以同等地位看待或族群中心主義已消失。這讓我回想起大三時的一個有關後現代都市文學的小組報告,我們的題目是有關眷村,實地走了一趟台北公館寶藏巖,也閱讀外省眷村第二代所寫的文學。在走訪眷村的經驗裡,遇見一個外省的老伯,我們於是隨即問了他關於眷村的環境以及他如何來台灣的過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滔滔不絕地談論當年撤退來台的精采實錄,他言談神情中可以看的出他對家鄉的眷戀與想再回去那塊土地的心情。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那次的訪談經驗其實看出了我們身為不了解眷村文化的年輕世代,雖然是抱著想要去了解的心態去接近他們,但也因所學知識與接觸經驗的狹隘,使得我們出發的角度依舊停留在當年那段往事,藉由不斷談論我們不熟悉的歷史而把他們視為與我們很遙遠的他者,忽略了現今在台灣的許多外省人面對自己外省與本省間的認同是會隨時空不同已有所改變,如同朱天心的小說<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透露了身為外省第二代他們心中雖對眷村有眷戀,但同時生在台灣這片土地他們也想認同自己是個台灣人,可是卻在面臨族群對立的情況下遭逢很多阻礙。
因此年輕一代之間雖然族群概念模糊,同時又對於我族與他族文化認識之淺薄,造成表面看似沒有差異,但在認真談論族群時仍會使得潛意識裡狹隘的族群中心主義顯露無疑,用自己唯一的族群知識去看待族群關係,造成對同是生長在這塊土地其他族群的刻板延續與複製,就如同每當選舉都會把族群對立的議題拿出來炒作一樣,只會把歷史的傷害不斷加深。
結語
許多過往看似自然的族群認同行為,經過反思後才驚覺背後都有許多社會權力結構的運作,就像是我會認同父親而非母親(父權意識)﹔我雖有外省血統卻對學習福建話沒興趣(不具語言的主流利益)。語言雖是我族群認同的重要指標,卻也因城鄉地域不同令我去思考自己過往的台灣人認同,才發現其中摻雜有從都市優越主義出發所產生曖昧模糊的矛盾情感(會說閩南語,卻不以此為高尚或光榮的),同時以會說閩南語的台灣人認同感也會因為地域的改變(北部移到南部)程度有所削減,看出城鄉差異的確會對認同的內容與強度有所影響。最後,年輕一輩雖已不若以往身處於政治對立的環境中,但某些時候還是會因族群知識的不足而暴露潛意識的族群中心主義,無形中可能間接造成對他族的壓迫,因此要做到容納肯認多元的存在並不只是表面功夫,還需要更時時去檢視自己在選擇族群認同背後的權力運作,才能真正意識到我群跟他群存在的關係並做出真正的反省。
參考書目
朱天心,1992,《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麥田。
|
本計畫由教育部 「新移民與多元文化計畫」顧問室支持 |
|
Program iSCD Office is supported by MOE. |
|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copyright ©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
|
如有任何問題請與網站管理員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