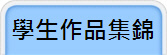移民人權:族群與多元文化的觀點
Human Rights for Immigrants: Ethnic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備註:學生名字皆以匿名方式處理]
家偉的族群經驗與族群認同
我的家庭成員與成長環境
當家庭成員都有閩南人(亦稱福佬人)的血緣時,閩南人的族群文化或許可以從我的家庭結構與活動窺之一二。
爺爺與奶奶在結婚前分別居住在彰化縣○○○的不同村落裡,婚後育有四子二女[1],其小孩成年後,都各自與鎮上不同村落的男性與女性結婚,且依據傳統禮俗「從夫居」生活在鎮上。
我出生在農村的大家庭裡,稻米一直是我們家的主食,且有自己的農田種植稻米,爺爺配合季節從翻土、引水灌溉、插秧、施肥、除蟲(通常是田螺)、收割、曬穀、販賣等形成一套傳統種植稻米的文化,同時我以一個「半調子」、「幫忙協助」的農家子弟角色參與上述的部分過程,乃因身為家中長子長孫的我被賦予唸書的期待,而不是成為一個農村裡的農夫,且不是搬貨物的運輸工人[2]。
族群的語言:台語、國語
家庭是由婚姻、血緣或收養關係所組成的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高福明、包素蘭、洪劍、胡皖萍,2003:115),更是族群文化傳承的載體,例如:語言的教導。
我們家是閩南文化的家庭,所以講台語?從小與家人、親戚、鄰居都是以台語作為溝通的語言,例如:阿嬤、阿公、阿爸、阿母、阿叔、阿姑等稱謂。爾後接受幼稚園與國民小學教育,學校教導「ㄅㄆㄇㄈㄉㄊㄋㄌ…..」的國語注音符號與發音,使我開始學習寫注音、寫國字、講國語,漸漸地國語成為我主要的溝通語言,也開始會用國語跟家人聊天。但是,與爺爺、奶奶聊天時,仍反射性地用台語暢言。
然而,有一次堂弟(三叔的小孩,即爺爺與奶奶的孫子,約莫五歲)跟奶奶聊天的時候,因為只會講國語,不會講台語,被奶奶開玩笑稱之為「你是不是外省人的小孩?」其中隱含著希望自己的孫子會說台語,彷彿外省人說國語,我們不是外省人要說台語。顯然地,以台語作為一種家族溝通的語言,其在鞏固閩南族群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在鞏固族群文化之間的差異。實則早年國民教育不教導、工業化與都市化的來臨導致核心家庭的普遍、使家庭中的小孩少與老人家聊天等因素是台語成為弱勢語言的原因之一。
閩南文化
家庭提供唸書的資源、環境,甚少要求我幫忙家務,終於高中聯考放榜,我進入彰化高中就讀,同時階段性地宣告且滿足他人的期待:農夫、工人不是我未來的工作以及家庭的階級地位可以往上流動的可能性。
此外,滿18歲的高三那一年,爺爺奶奶為我舉行成年禮儀式,宣告我正式成為一個大人。當天住家房子前面的桌上擺滿著一盤一盤的水果、兩頭嘴巴咬著柳橙的豬、兩隻頭上掛著麵線的假羊與一個有一層樓高的祭祀法壇。祭典開始時,我端著祭祀用的盤子且插著香,一邊聽著法師誦經,一邊跟著法師身後繞著法壇走,且跟隨在我身後的人有:弟弟、堂弟們、二叔、三叔、四叔等。
我生活在一個閩南文化的家庭裡,我的成年禮透露一個根深蒂固的閩南(福佬)文化,一個長子長孫的身分地位是不同於其他孫子,且自從這一次成年禮之後,再也沒有其他孫子的成年禮被舉行。
我的家庭文化就是一個縮小的閩南族群文化,當我從小生活在其中時,我察覺不到其他文化的存在,我從小就這樣被教導怎麼過一個閩南人的生活文化,一個多數優勢的閩南文化,且甚少質疑之。
最近當我奶奶跟我說:「不可以與屬豬的女孩子結婚。」我不僅感受到異性戀婚姻家庭的預設,且瞭解閩南文化對於家庭與結婚的重視,例如:二叔與二嬸、三叔與三嬸、以及四叔與四嬸在結婚前,雙方皆交換彼此的生辰八字,以卜八字是否相配?此稱之為「合婚」,且表達了傳統的閩南人相信生肖、生辰八字等命格對於家庭幸福美滿的影響力。
客家人、原住民、還有我
一個族群有相對的優勢(如:人數上的優勢)與相對的弱勢(如:台語非官方語言),當我生活在自己的農村裡,我無法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體認不到族群的差異,差異對我而言不深刻,甚至是不存在。
雖然歷史與地理課教導了台灣有許多的原住民,國外也有許多的民族,然而在農村的生活中,卻從來沒有真實的出現過一位台灣原住民,更別提「外國人」的出現,因為我們家附近居住的居民幾乎都是親戚,其中有陳氏與鄭氏兩大家族,因此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往往是經由課本的照片與文字得知。直到我離家背井來到高雄就讀大學之後,出現了一道曙光。
於新生座談的自我介紹結束後,我被台下的同學詢問:「你是那裡人?」我回答:「我是彰化人。」卻引發另外一位同學的聲音:「你沒有彰化腔耶!」同樣都是閩南人,可能講台語或者國語,卻因地緣的關係而有不類似的語調。
而下一位同學介紹自己是「客家人」的時候,卻引來了一陣喧嘩:「妳會講客家話嗎?」、「客家的名產是什麼?」、「妳們家住那裡?」等問句。
當答案的揭曉沒有滿足問話同學的期待,一個不會講客家話的○○人,她跟我們一樣講國語。語言的障礙是否否定了一個身為客家人的認同呢?就像我奶奶覺得「不會講台語的孫子就像外省人的孩子一樣」。然而並非所有的客家人都會講客家話,或者是所有的原住民都會講原民語一樣。
由於全球化,我們開始學習英文作為溝通的第二語言,然而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意指著語言與認同之間的關係被分離了,但是語言不會僅成為一種溝通的工具,它的確是一個族群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必須理解與省思的是「一個文化的語言為何會形成斷層?」
第一次與原住民交談時,他/她們也跟我一樣講國語,唱國語歌。從外觀而言,外國人很明顯可看出是外國人,然而台灣原住民則不明顯,因為有的人可以明顯地從面貌辨識原住民的特徵,例如:排灣族膚色較黑,有的則不行。從小認為台灣原住民跟我一樣生活在台灣,沒有文化的差異,且原住民在清明節也會掃墓,然而經由大學認識的原住民學妹的說明,才驚覺族群的文化差異有一段距離,爾後逐漸把原住民視為跟我們不一樣的族群,不論在文化、資源、就業機會等。
我是閩南人/彰化人/男性?
每年我都會參與觀賞原住民的活動,當她/他們開始唱歌或者跳舞時,總會先介紹自己的漢名與原住民的名字,同時說明自己是那一族的人,然後會贏得同族與不同族人(原住民)的掌聲與歡呼,雖然是不同族群,但其以「原住民」作為彼此連結的平台。
此外,高雄某大學的學生社團成員都有部分原住民的血統,且有強烈排斥非原住民參與社團,乃因每個族群都有其中心的認同主義:包括文化、血緣、語言等,導致想要參與原住民文化活動的我,對於參與原住民社團其實是有阻礙的。此時,我才真正意識到血緣系統對於一個民族的巨大影響力,而我深刻體認到我身是漢人(在歷史上曾經壓迫原住民生活環境的族群),有著不同於原住民的血緣關係與歷史背景。因此,認同隱含著兩個層次的意涵:其一為別人(如:原住民)怎麼看待我?其二為我怎麼看待自己?
我出生在那裡?我的父母親是誰?從事什麼樣的工作?這些問題都隱含著其他人認為「我是誰?我不是誰?我是那個民族?我不屬於那個民族」的概念。然而,我開始對「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產生質疑,似乎族群的認同與文化差異是經由社會化的過程被建構的,甚至內化成為我每天的日常生活。
我是彰化人,生活在一個勞工階級的家庭;若以血緣作為區分時,我又是漢人(閩南人),不同於台灣原住民,不同於客家人。而且似乎我們本來就在這裡,我們的家族本來就生活在這裡,但是我們的祖先從那裡來?直到詢問祖母,才得知一個大概的模糊答案:福建。
「我是閩南人」的認同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讓人無法覺察,因為我本身就是閩南人,我就是這樣被閩南文化養大的。因此,對我而言不同族群的存在不是那麼地深刻,因為大家使用的語言幾乎都是國語或台語,是我熟悉的語言。
參考資料:
高福明、包素蘭、洪劍、胡皖萍(2003)《中國婚姻家庭》。合肥:安徽教育。
|
本計畫由教育部 「新移民與多元文化計畫」顧問室支持 |
|
Program iSCD Office is supported by MOE. |
|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copyright ©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
|
如有任何問題請與網站管理員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