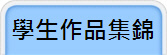移民人權:族群與多元文化的觀點
Human Rights for Immigrants: Ethnic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備註:學生名字皆以匿名方式處理]
雯妤的族群經驗與族群認同
一、前言
關於目前的台灣族群分類,王甫昌(1998)指出現今所謂的四大族群,其實包含了三種不同層次的說法:原住民/漢人;本省人/外省人;(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而且這些分類的背後,都有其特別的歷史與社會背景。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每一組分類的產生,都是由自認「弱勢」的一方所界定出來的,因此,當我們習慣稱之為「四大族群」時,仍然不能忽略個別間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權力關係。台灣的族群關係中,族群意象、語言文化、歷史記憶以及政治行為,更是造就「四大族群」的重要面向(王甫昌,2002),本文特別重於本省與外省的族群建構,試圖以自身的成長經驗,與台灣的族群、政經發展互為對照,並試著解釋新一代族群認同的轉變。
二、「本省人」的建構與認同
我在家中排行最小,上有兩位姊姊[1],與我相差五、六歲。我的父親是農家弟子,出生於彰化○○,由於祖父早年罹癌逝世,祖母一肩扛起撫養六個男孩的重責大任,因此父親五專畢業後,便北上謀職。而外公為公務人員,身為長女的母親,在嘉義○○畢業後,亦離家到台北工作。台灣五十年代土地改革後,父母兩人於民國五十末、六十年代初期踏入職場,正好搭上六十年代快速資本化的順風車,晉身成為中產階級[2](徐正光,1989)。
民國七十年代[3],父親轉業為自營商,並於板橋開業定居,「頭家兼工人」接訂單、送貨都自己動手。炎炎夏日的午後,父親常在客廳地板鋪上草蓆休憩,一邊放著「綠色和平」電台的廣播節目,就連開貨車載我上英文課的路途,我一邊複習著當天的考試內容,一邊得聽著有些「惱人」的地下電台。雖然我並不喜歡那些感覺很沒「水準」的廣播,但從這些資訊,我很小就知道父親有著挺民進黨的深綠政治立場,每到競選,家中也不乏綠色的競選旗幟,以及阿扁娃娃。雖然老媽不聽電台,但他從小便灌輸著政府遷台外省人取得優勢所造成的不平等(老媽指著電視主播沈春華,告訴我電視台要外省人才進的去,有著本省人的口音與背景,是不符合要求的)。而雙親的政治色彩,也「感染」了家中的三姊妹,因此我的「本省人」身分認同,絕大部分是源自於雙親的影響。
從小我就耳濡目染福佬文化,包括祭拜祖先[4]等在生活中都有所接觸,但在我身後最明顯的族群認同,就屬政治行為。鬱鬱寡歡的高中生涯,當時競選台北市長連任的陳水扁,便成為我的精神寄託,我竟瘋狂地把他的競選貼紙,黏在書包的內翻面,而競選連任失利,也讓當時的我認為是一種當前的學業劣勢無法翻轉的預告。公元兩千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恰好與我順遂的大學生涯作為對照,使我與民進黨的存亡,竟有種「生命共同體」的巧合與感慨。即便現在已經「減綠」,對執政與在野黨都抱著質疑的觀點,但政黨立場似乎已經難以翻轉,「本省人」的身分認同,也根深蒂固。
三、外省/本省的建構與分析
在我的生命歷程中,最明顯的是「外省」與「本省」認同的區隔,而客家人與原住民在其中是隱微的,這也突顯著其的社經劣勢,邊緣化的位置讓人忽略。Ruth(1993)指出與階級經驗建構出種族,這樣的關係中,也形塑出他者與自己的對照,亦伴隨著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展演。
本省與外省的對立,源自於民國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陳儀政權對於外省人偏頗,排拒本省所積累的民怨,但是在反攻大陸的前提下,本省族群的意識並未持續擴散,一直要到民國六十年代中後開始要求國民黨政治民主化與自由,以及六十八年的「美麗島事件」,集結起本土的激進意識,才逐步地發酵(王甫昌,1998)。對於外省人的印象,我從母親那接收到「不要嫁外省人[5]」,以及「外省人佔具特權」的兩種論述,但是親身接觸的榮民,卻被我歸於「外省人的下層」,並未意識到所謂「佔據特權的外省人」,其實只是一小部分的人。趙剛、侯念祖(1995)便嚴正聲明,必須要意識到外省族群中的異質性,他們指出「將所有的外省人視為「外省權貴」則不但排除了中低層的非眷村外省人,更排除了社會底層的自謀生活退伍士官兵」。趙剛和侯念祖的說法,點醒了我,也讓我深思,為何從未見過眷村生活的我(參觀過花蓮榮民之家),能夠將榮民區別於「特權階級」,但對於其他外省人,卻仍抱持著整體特權一致性的想像?這個答案,可能源自於接觸張愛玲、白先勇等「權貴」作家的小說,因此對於外省人,便形成普同性的優渥、受國家庇護之想像。
在求學階段,由於都市學校皆使用國語,因此外省人、客家人、本省人之間,身分是隱匿的(更沒有原住民血統的同學),除了高中、大學開始有同學表露自己的政治立場與族群身分,整體而言在學校的生活中,並沒有明顯的族群間的對立,反倒是以政治立場的不同[6]作為成為區辨的可能。在學校中最明顯的「階級」對立,是以學業成績作為考量,這也可能是使得族群差異模糊的可能性之一。不過相對於我在學校的「未感知」,大姊高中就讀於台北某知名女校,他曾表示班上的同學幾乎都為外省人,並以此組成結構向我訴說本省與外省間仍有差距。
然而,我們仍必須注意到,民國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以及六十年代後的政經變化,以及職業型態的劇烈改變,使得外省第二代,面臨認同危機。趙剛、侯念祖(1995)指出外省第二代未進入軍公教等職業,便必須學習台語,以靠攏中產福佬,作為輔助提昇社會地位的利器。因此,我們必須檢視所謂佔據優勢階級的外省人,其實是指外省第一代的某些少部分的人,然而絕大部分的外省人在第二代以後,光景不再,甚至必須面對自己的認同危機。台灣中產階級的形成,使得本省族群在教育、政治以及經濟方面重新洗牌,亦在資源的大餅取得,得以分一杯羹。
相較於父母輩對於省籍情結的敏感,在新一代的身上,似乎對於族群的認同更為薄弱,僅存表面的認同,當涉及政治議題,才有較明顯的區別。王甫昌(2002)認為,新一代的本省人並未經歷上一代的族群矛盾,另外社會互動的頻繁,亦有助於族群敵意的消弭,只剩政治場域的競逐,而未能擴散到其他部分。此外,我認為全球化下,競爭的場域已經演變成跨國的角力,資訊流通的龐雜,亦使得對立的族群觀點早已非日常生活的重心。對照著政治上不斷被冷飯熱炒的族群對立,總是老掉牙的戲碼,只能挖掘的歷史事件作為立場的捍衛,身邊充斥的族群論述,也並無新意。
族群對立的削弱,並不代表對立不存在。我們所用的語言與文化,以及歷史記憶,仍然形塑著我們族群的認同,只是展演的方式已改變或有所侷限。這也呼應了Ruth(1993)所說的環境之可動性,使得經驗複雜化,可被遺忘、指稱,或是透過概念而轉換。
[1] 大姐為成功大學○○博士班學生,二姊為台北市立○○國中老師,並一面攻讀台灣師範大學○○系碩士。
[2] 以徐正光(1989)的分類,父母屬其第一種分類:國家部門和私人企業部門所雇用的中上級工作人員。
[3] 我是民國72年出生,當時台灣經濟發展蓬勃,父親的生意正往上爬,常常半夜當還得出門送貨。
[4] 趙剛,侯念祖(1995),特別突顯外省與本省祭拜祖先的差異性。
[5] 母親並沒有提出外省人「不好」的說法,只是突顯外省與本省「不一樣」的對立。
[6] 用「不同」而不用「對立」,是因為我的生命經驗中,同學間並沒有人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爆發激烈衝突。
參考文獻
徐正光(1989)<中產階級興起的政治經濟學>,蕭新煌(主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33-47。台北:巨流。
趙剛、侯念祖(1995)<認同政治的羔羊:父權體制與論述下的眷村女性>,《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19:125-163。
王甫昌(1998年12月)<光復後台灣族群意識的形成>,《歷史月刊》「台灣族群關係的回顧與展望」專題,131:30-40。
王甫昌(2002年12月),《台灣社會學》邁向台灣族群關係的在地研究與理論:「族群與社會」專題導讀,4: 1-10。
Frankenberg Ruth,1993
White women , race matter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
Minneapolis:
“Growing up White”.
|
本計畫由教育部 「新移民與多元文化計畫」顧問室支持 |
|
Program iSCD Office is supported by MOE. |
|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copyright ©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
|
如有任何問題請與網站管理員聯絡。 |